9月16日,諸城土墻社區,兩名農民坐在他們的庭院附近。不遠處,要讓農民集中住的樓房正在建設中。
9月15日,山東諸城枳溝二村,一名農民在瓦礫上吃午飯。他當天在整理建筑垃圾,尋找可用的材料。
一場讓農民“上樓”的行動,正在全國二十多個省市進行。
拆村并居,無數村莊正從中國廣袤的土地上消失,無數農民正在“被上樓”。
各地目標相同:將農民的宅基地復墾,用增加的耕地,換取城鎮建設用地指標。他們共同的政策依據是,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。
記者調查發現,這項政策被地方政府利用、“曲解”,成為以地生財的新途徑。有的地方突破指標范圍,甚至無指標而“掛鉤”,違背農民意愿,強拆民居拿走宅基地。演變為一場新的圈地運動。
宅基地轉化后的增值收益,被權力和資本“合謀”拿走。農民則住進了被選擇的“新農村”,過著被產生的“新生活”。
專家指出,這是一次對農村的掠奪,強迫農民上樓并大規模取消自然村,不僅與法治精神相違背,對農村社會也將帶來巨大負面影響。
10月,走在山東、河北、安徽等地,會發現一些高層小區在農村拔地而起。
在河北廊坊,2006年被評為河北省生態文明村的董家務村,如今已成一片廢墟,大片新修的村居在鏟車下倒塌,剛修好的“村村通”水泥路被鏟平。
山東諸城市取消了行政村編制,1249個村,合并為208個農村社區。諸城70萬農民都將告別自己的村莊,搬遷到“社區小區”。
如今,像諸城這樣的“拆村并居”,正在全國二十多省市進行。
今年8月份在海口舉行的“城鄉一體化:趨勢與挑戰”國際論壇上,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陳錫文指出,和平時期大規模的村莊撤并運動“古今中外,史無前例”。
此前,今年兩會期間,陳錫文指出,在這場讓農民上樓運動的背后,實質是把農村建設用地倒過來給城鎮用,弄得村莊稀里嘩啦,如不有效遏制,“恐怕要出大事。”
拆村并居風潮
各地規模浩大的拆村運動,打著各種旗號,例如城鄉統籌、新農村建設、舊村改造、小城鎮化等。
也有對應政策推出,諸如“村改社”、“宅基地換房”、“土地換社保”等等。
各地都在規劃著,要在一個很短的期限內,將域內農村“大變樣”,民居改樓房。
這樣的運動熱情,與各省市對國土資源部(下稱國土部)一項政策的“歡迎”密切相關: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。
2006年4月,山東、天津、江蘇、湖北、四川五省市被國土部列為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第一批試點。
國土部2008年6月頒布了《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管理辦法》(以下簡稱增減掛鉤辦法),2008、2009年國土部又分別批準了19省加入增減掛鉤試點。
按照國土部文件,“增減掛鉤”是指,“將擬整理復墾為耕地的農村建設用地地塊(即拆舊地塊)和擬用于城鎮建設的地塊(即建新地塊)等面積共同組成建新拆舊項目區,在保證項目區內各類土地面積平衡的基礎上,終實現增加耕地有效面積……節約集約利用建設用地,城鄉用地布局更合理的目標。”
也就是,將農村建設用地與城鎮建設用地直接掛鉤,若農村整理復墾建設用地增加了耕地,城鎮可對應增加相應面積建設用地。
該政策得到地方政府盛情歡迎,各個省市、各級政府均成立了以主要領導牽頭的土地整理小組。對應的地方政策、措施也紛紛出臺,目的明確:讓農民上樓,節約出的宅基地復墾,換取城市建設用地指標。
去年,河北提出在全省開展農村“新民居”工程。據介紹,“新民居”與山東“村改社”一樣,都是在增減掛鉤框架內,增加建設用地指標。
據河北省國土資源廳透露,到2012年,保守估算,新民居工程將為該省增加建設用地50多萬畝。
土地財政的“稻草”
在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之前,嘗到土地財政甜頭的地方政府,都在辛苦“尋找”土地中。
近年來,我國耕地保護與經濟發展用地的矛盾發展到很尖銳的程度。如何“找地”,也成為各地國土部門的首要任務。
以河北省為例,2009年需要新增用地約為21萬畝,但國家指標17萬畝。如何填補4萬畝的缺口,成為河北投資項目落地的難題。
“增減掛鉤”一經出臺,立即成為各地破解土地瓶頸的“金鑰匙”。
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,必須獲得國土部批準,得到相應周轉指標后,才能開展。指標是“借”,3年內要以復墾的耕地“歸還”。
根據媒體報道,去年3月,河北、遼寧等13個省份新獲國土部“增減掛鉤周轉指標”15.275萬畝,當年國土部還有第二、第三批指標下達。
河北申請到1.2萬畝指標,成為解決土地缺口的一個有效途徑。
山東肥城市國土資源局局長翟廣西說,肥城每年用地需求3000至4000畝,每年的用地指標僅400至500畝。他說:“如果不是增減掛鉤試點,我這個國土資源系統的‘生產隊長’真就為難了。”
山東諸城市土地儲備中心主任安文豐稱,將農民全部集中居住后,保守估計,諸城將騰出8萬畝舊宅基地。通過土地級差,政府每年土地收益有兩三億元。
被奪宅基地的農民
根據國土部的試點管理辦法,增減掛鉤嚴禁違背農民意愿、大拆大建。但在一些地方,強拆民房,強迫農民“上樓”的事例,已有發生。
管理辦法要求,要在農村建設用地整理復墾潛力較大的地區試點,現實中,不顧實際情況,“一刀切”拆并村莊的做法,非常普遍。
管理辦法還要求,妥善補償和安置農民,所得收益要返還農村,“要用于農村和基礎設施建設”。但在有些地方,政府拿走宅基地利益的同時,甚至還要求農民交錢住樓房。
在江蘇省邳州市壩頭村,村莊被整體拆遷,當地建設了數十棟密集的農民公寓,要村民補差價購買。
因補償款購買不起足額面積樓房,壩頭村35歲女子徐傳玲去年10月自殺。今年1月,當地強制農民上樓,十多人被打傷住院。
今年1月18日,壩頭村村民王素梅告訴記者,她的丈夫被拆遷隊打傷,后又被村干部拉到湖邊要求立即簽字,否則沉湖。
就在近期,山東也發生了毆打農民的暴力事件。
除被要求交出宅基地之外,今后,農民要獲得宅基地,將成為難題。在全國多個地方,宅基地上建筑不再批準動“一磚一瓦”,也不另批宅基地。村民如有住房需求,需要拿宅基地住房換樓房。
失去宅基地的農民,還將面臨生活、生產方式轉變。對于長期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來說,生活成本增加和耕種不便,成為現實問題。
增減掛鉤是“無奈選擇”
中國農業大學教授郝晉珉參與了“增減掛鉤辦法”的制訂工作。他認為,國土部開展此試點也是無奈的選擇。
“經濟發展用地要保證,耕地和糧食安全也要保證,空間就這么大、土地就這么多,該怎么解決?”郝晉珉稱,經過多方比較選擇,增減掛鉤是比較有效的解決辦法。
2004年,國務院《關于深化改革嚴格土地管理的決定》提出“鼓勵農村建設用地整理,城鎮建設用地增加要與農村建設用地減少相掛鉤”。
2006年,國土部確定了首批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試點省份。2008年底,國家4萬億經濟刺激方案出臺之后,國土部也推出了一系列制度,其中為重要的,是加大了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周轉指標。
國土部土地整理中心副主任鄖文聚說,大規模“借出”周轉指標,是國土部的策略,是為應對近兩年用地壓力和許多不可測因素。
今年7月,在大連召開的國土資源廳局長會議上,國土部部長徐紹史稱,解決地方經濟發展對土地需要的迫切問題,主要方式之一,就是增減掛鉤試點。
國土部官員在該座談會上通報稱,增減掛鉤從一定程度上滿足了地方對經濟發展帶來的用地需求。
“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。”國土部法律中心首席顧問楊重光曾對媒體說,要保持住宏觀經濟發展,就一定會造成土地需求的緊張。
今年6月26日,國土部總規劃師胡存智在“中國房地產2010年夏季峰會”上透露,通過增減掛鉤,大約有2700萬畝的農村建設用地,將納入城市建設用地當中。
截至今年6月底,國土部新批了增減掛鉤試點第三期18個項目。與第一期和第二期不同的是,國土部將周轉指標下達給了省,由省確定試點項目報國土部批準。
“漏洞必須堵住”
今年5月底,國土部的9個調研組,對現有24個增減掛鉤試點省份進行了快速調研,發現了不少問題。
試點要求指標“三年歸還”,那么,到2009年底,第一批試點周轉指標應已全部歸還。但第一批試點僅拆舊復墾5.58萬畝,約占下達周轉指標的80%。
在6月份的一次部長工作會議上,國土部部長徐紹史說,當前的掛鉤試點中,還存在地方在批準試點之外擅自開展掛鉤,以及違反規定跨縣域調劑使用周轉指標等問題。
徐紹史再次強調,增減掛鉤后的土地級差收益,要返還,用于改善農村生產生活條件。
國土部土地勘察院副總工程師鄒曉云曾對媒體表示,在增減掛鉤指標的使用上,存在一定漏洞,本末倒置,導致地方政府以獲得建設用地指標為目的,“這樣的漏洞必須堵住”。
2008年初,國務院辦公廳就下發通知,要求嚴格執行有關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法律和政策。其中國辦關注到,一些地方利用增減掛鉤試點,擅自擴大建設用地。
記者在各地調查也發現,有的地方利用“掛鉤”政策,再次占用耕地,并擴大建設用地范圍。
在6月份的會議上,徐紹史強調,下一步周轉指標將被作為各省年度用地計劃指標的一種,納入各地用地計劃統一管理。各地再也不能將周轉指標作為“天上掉的餡餅”。
溫家 寶總理曾說,“在土地問題上,我們絕不能犯不可改正的歷史性錯誤,遺禍子孫后代。”這是總理2007年為確保18億畝耕地紅線所說的一句話。
對于各地圈走農民宅基地、大拆民居的做法,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陳錫文在今年兩會時就疾呼要“急剎車”。
在今后的“十二五”期間,如何在保障農民利益前提下,真正城鄉統籌發展,將是擺在各地政府面前的一個嚴峻課題。
9月15日下午,諸城枳溝西社區農民王蘇前,拿著鐮刀從三樓的住房走出。
他在擠滿農用車的樓道里,找出了自己的那輛,準備去兩公里外的農田干活。
這是一片新蓋的樓房。5棟6層樓,包著一片小廣場。
枳溝西社區81戶村民9月初搬遷到此。此前他們住在兩公里外的枳溝二村,每家有近200平方米的四合院。如今他們的原住宅已被鏟平,騰出的宅基地今秋將復墾種小麥。
近70歲的王蘇前大字不識幾個,他聽人說國家有政策,農村每多出一畝耕地,將獲獎勵20萬元。他不理解的是,好好的院落都拆了,再建新樓,“這不是浪費錢?”
算不清賬的王蘇前,以為村里是在騙取國家資金。
他不知道的是,整個諸城都將“村改社”。雖然大家的農民身份不變,但都將搬進樓房住。由此增加的建設用地,讓政府每年能有兩三億元的收入。
【拆村】制造208個“萬人村”
王蘇前他們的樓房,只是諸城枳溝西社區集中住宅的一期工程。
9月16日,在這片小區的對面,社區規劃圖上標注著近百棟高層住宅。今后這個社區合并的5個村莊的村民,將全部搬遷到此。
今年6月,諸城市對外宣布,全市1249個行政村全部撤銷,成立208個農村社區。每個社區以2公里為半徑,涵蓋5個村莊、約1500戶,近萬人。
每個社區集中居住,由政府出資建設社區服務中心,同時還建幼兒園、老年活動室等。
9月15日,距離諸城市區東部20公里外的大米溝社區,一片農田內聳立起四棟4層小樓。這是這個社區近期剛建好的集中住宅,社區內的居民尚沒有一戶進去居住。
在大米溝社區服務中心旁,布告欄上張貼的規劃圖顯示,整個社區將建設20多棟5層以上的樓房。
當日,諸城大楊家莊子社區一楊姓工作人員介紹,社區計劃建設住房9.8萬平方米,總投入預計9000多萬元,如今一期工程已完工。社區全部建成后,將吸納周邊4個村全部農戶。
如今在諸城農村社區的中心村內,顯眼的就是正在興建的樓房工地。
9月16日,諸城土墻社區、大辛莊子社區、大米溝社區、紅星社區等地都在開工建設住宅樓,以5層居多,其中紅星社區的住宅樓高12層。
受訪的村民說,目前各村都在動員搬遷。
走在諸城的鄉間,多數村居是黃墻紅瓦,一排排四合院排列十分整齊。
9月16日,諸城大辛莊子社區村民李寶菊說,諸城現在的整齊劃一的村居,是經過3次農村規劃后形成的。這樣的村子內,基本沒有浪費的空地。
9月17日,諸城市宣傳部副部長王樹偉承認,其他地方“空心村”的現象,在諸城市并不存在。
不過,這些整齊的村莊,今后都將面臨被拆遷的命運。
據介紹,諸城已有78個社區開工建設住宅樓,數量達到近千棟,建成后可以容納1.8萬戶居民。
今年底前諸城將有萬戶以上居民住進樓房。他們原有的宅基地都將拆遷復墾。
【強制】農民被“打”上樓
王蘇前是同意住樓房的村民之一。他原有宅基地178平方米,不過4間房屋年久失修。
這次村里鼓勵搬遷,每戶村民無論原房屋新舊和大小,均獲同樣補償:一套80平方米住房和一個15平方米的庫房。
9月15日,王蘇前說,村里同意搬遷的人占多數。一些房屋破舊的村民和長期在外打工的年輕人,愿意上樓住。
村里還有部分村民不愿住樓房,村干部對他們說,村里超過70%村民同意,只能“少數服從多數”。
如今,在枳溝二村的舊村里,還有蘇、朱、郭三戶居民堅守。這三戶居民有兩戶剛翻修過住房,他們不愿接受同等補償,另外一戶則祖孫四代居住在8間房中,搬進80平方米的房子住不下。
王蘇前說,當初拆遷時,村干部動員稱9月7日前搬的,免一年供暖費,大家就紛紛開始遷。后來村里停水停電,剩下的住戶也不得不搬走。
9月16日,山東諸城紅星社區村民周洪發拿出一百多份村民的意見書,上書:“堅決不拆平房,不住高樓”。
當日,村民殷紅發指著臉上傷疤說,8月22日,村支書周金發帶領82人強行把村民的果樹、楊樹砍掉,他們上前阻攔,多名村民被打傷。
在紅星社區北邊,一片12層的高層住宅樓正在動工。周洪發說,村民將被安置在上面三層,剩下的房對外出售。
據介紹,從今年開始,諸城市規定各村老宅基地上不準再動一磚一瓦,也不批新的宅基地。村民要住新房,就要拿自己的宅基地換樓房。
土墻村一名李姓村民說,村里還沒有強制搬遷,但原村不再建設,今后肯定都會逐漸向樓上遷移。
【利益】8萬畝地的市值期待
在諸城市農民王蘇前眼中,全市要大規模建樓房不現實,“政府哪有那么多錢蓋樓房?”
他不知道,在這背后,地方政府還有另外一筆經濟賬。
9月17日,諸城市宣傳中心主任郭沛盛說,諸城主要以市財政投資建社區樓,今后將依靠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,農村多出的耕地,城市相應多出建設用地。用于社區建設的資金,將從增加的建設用地中找補。
據《濰坊日報》報道,諸城市土地儲備中心主任安文豐稱,如果農民全部遷到社區中心村居住,保守估計,將騰出8萬畝舊宅基地復墾為耕地。
下一步,他們將以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試點為抓手,每年復墾舊村址4300畝,每年節余將達3000畝建設用地指標。每年的土地收益有兩三億元。
9月16日,諸城市一名要求匿名的官員稱,為了便于實現掛鉤試點的建新拆舊項目區設定,2007年諸城市調整行政區劃,撤并鄉鎮,將23個鄉鎮撤并為13個,鄉鎮平均面積擴大了近一倍。另外諸城市區三個街道辦合并郊區3個鄉鎮,向農村延伸了近20公里。這三個街道辦的外延使諸城市區面積擴大到68平方公里。
諸城還將在農村土地上新建的住宅樓,有一部分對外出售。
9月17日,土墻社區售樓處的工作人員介紹,社區建設了3900多套住宅,將提供給剛剛并入土墻社區的五個行政村共1100多戶居民。剩下的住房,將對外出售,但沒有產權。
據了解,一些社區樓房經過土地變更手續后,非農業戶口人員以后也可購買。
對于集體建設用地流轉,現行法律仍是限制和禁止性規定。《土地管理法》規定,集體土地使用權不得出讓、轉讓或出租用于非農建設。
有專家認為,利用增減掛鉤置換出的建設用地,如進行商業開發,仍需按征地手續,繳納土地出讓金后才能變為國有。否則不能進行市場買賣。
9月16日,在枳溝西社區,小區里一棟樓房作為小產權房對外出售,每平方米1500元左右。買房的,多數是枳溝鎮的教師和商戶。
【改變】被制造的“新生活”
據了解,諸城市政府為了吸引村民快速搬遷,出臺優惠政策,如果一次拆遷能夠超過30畝地,那么每戶居民一畝宅基地的補貼標準將達到20萬元。
按照目前樓房每平方米約1100元的價格,村民基本不用出錢,能換得120平方米的房。
盡管如此,說服農民到樓上居住困難仍然不小。
如今,土墻社區的拆遷進度不到十分之一,入住樓房的只80多戶。9月17日,土墻社區村民說,要讓村民住進樓房,補償方案不能一刀切,村民宅基地上的建筑,也要拿出補償標準來。
據王蘇前說,他們置換的住房,沒有宅基地證,也沒有房產證。只有一張集體土地證。他稱,要辦房產證,每戶仍需再交2萬元。
“沒了牲口和家畜,做飯暖炕又不能燒柴。”9月15日,王蘇前粗略估算了一下,住樓開支每年至少要多花5000元。
王蘇前說,住進樓房以后水、電、氣、暖全部需要交費。現在小區內還沒有物業,搬進來半個月不到,院子里剩菜垃圾亂丟,今后請物業公司仍需要錢。
據王蘇前講,住進小區的村民,大半個月來基本都沒有去幾公里外的地里做農活,他覺得“不能一腿泥就上樓呀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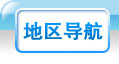
 您的位置:
山東技校網 >> 時事熱點 >> 多省市強行撤村并居
您的位置:
山東技校網 >> 時事熱點 >> 多省市強行撤村并居


 公安備案號 13024002000224
ICP經營許可證號 冀B2-20170024
網站備案號 冀ICP備11020808號-9
公安備案號 13024002000224
ICP經營許可證號 冀B2-20170024
網站備案號 冀ICP備11020808號-9

